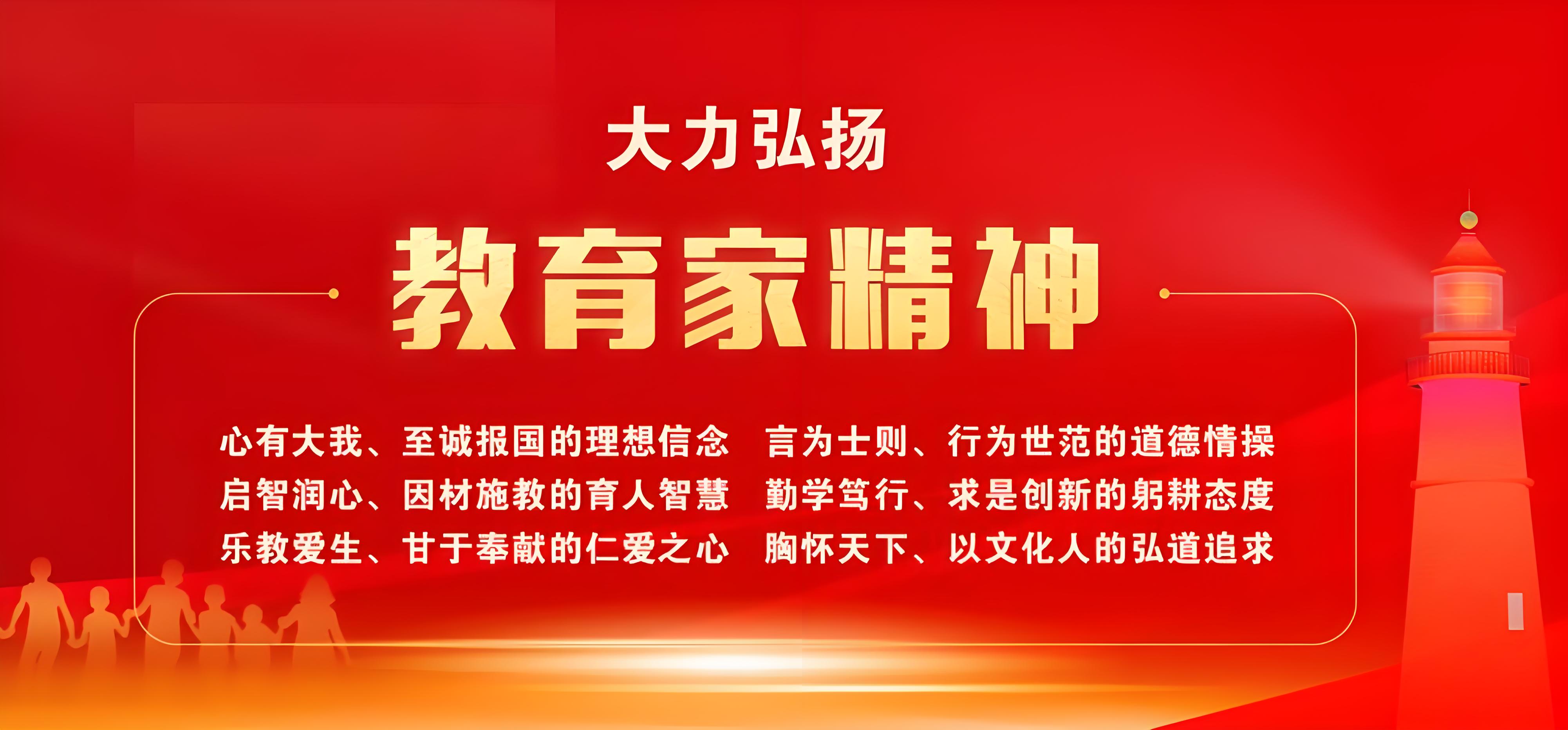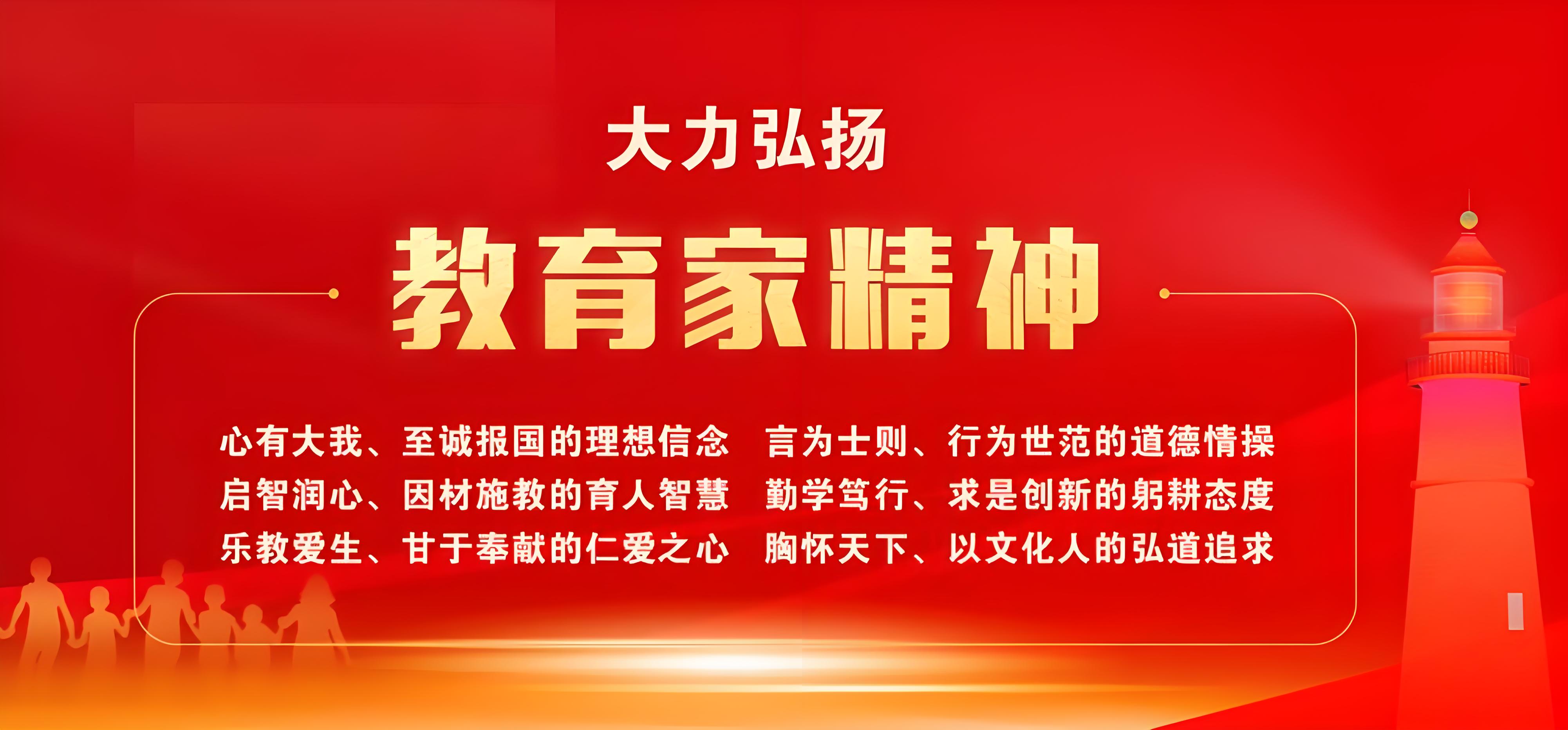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文法系202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
叶悦儿
我们计划花三天的时间翻过夹金山。一开始是原始森林,一片片,一丛丛,铺撒在浩瀚的六月雪中,奇特的景色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,大家劲头都很足。可一过中午,天气骤变。先是大雾弥漫,能看见的不过是身前身后的几个人影。随后是毛毛细雨,转眼却又变成了霏霏白雪,大风杂夹着雪向我们刮来,刮在脸上仿佛如刀子割一般,我们根本不敢抬头,只能埋头赶路,我一不小心,一脚踩空,却没有掉下去,回头一看,是一个身影壮硕的男子拉住了我,脸很普通,但那双拉住我的手奇黑,仿佛溶在了夜色里。就这样,我认识了荣全哥。
赶路途中,夜晚我们烧起篝火聊天,讨论到战争胜利以后各人的事业。有人想说继续当兵,算个有始有终。有人想当个小官,因为他爸正好有官职在身,也算子承父业。有人想回家娶个老婆,做点小生意平平淡淡一辈子也就算了。有人想作徐良黄天霸,身穿夜行衣,反手接飞镖,以便劫富济贫。荣全哥以前是湘西辰溪县的一名煤矿工人,所以我问他是否会回湘西继续当一名煤矿工人。他伸手出来对我打了个响榧子,“以后的事就等以后再想,我这性命横顺是捡来的,能多活三十多年,这三十多年便算是我多赚的,活一日是一日罢的,哪要为以后作打算。”“你若真是那么豁达不计较,你那枚银元何苦一直藏着不花,你留着怕还是在为以后留后路罢了。”听我突然提起他那枚银元,他发愣了一下,随后扯起一个难看的笑容,说:“那可不是我的,我只是在替别人保管罢。”
“那个时候,国民党正好在湘西剿土匪,我就和四桥子商量着,看能不能趁乱捡点东西走。奥,四桥子,我在矿上一起工作的好兄弟。”荣全哥运气不好,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,只能灰溜溜的下山,却不想碰上了国民党的军官。旁边是一堆尸体,脑门上被顶着的是冰冷的枪口,身上是摸来摸去搜身的手。“我那时就在想,我每天,将近14年的时间,都在那个黑井里爬来爬去,抬头看到的只有那黑脸黑手脚、全身光裸、腰前围上一片破布、头上带一盏小灯的人。什么时候矿坑坍塌了,进水淹了,我们这些讨生活的人自然也就完事了,我这一辈子,也就这样过去了。我就想,如果我有下辈子,我肯定不去挖煤了。”
枪响了,共产党来了。
荣全哥在那堆尸体里看到了一双黑手。
“他死在哪,哪里就是他的坟了。我把他拖进坑里的时候,他的裤带里掉出个红布团子,我打开一看,就是这枚银元。”在荣全哥的家乡,螳螂是死去的亲人的化身。“等我给他填好土,抬头一看,不知道哪来的螳螂立在那,就那么看着我,那我还哪敢拿着这枚银元,他肯定是想让我把这枚银元带给他爸。”四桥子的妈一生下他就死了,家里穷也娶不上老婆,只有一个同样在煤矿里挖矿的爸。“我回到煤矿上,没几个人在那,我一打听,原来矿塌了,没人爬出来。”荣全哥拿着那枚银元加入了共产党。我们强渡乌江天险,四渡赤水,过金沙江大渡河,飞夺泸定桥,九死一生,那枚银元在他身上。我们过草地没粮食饿的吃青草,等青草吃完了又拔枯草的草根吃,那枚银元在他身上。等荣全哥死在腊子口,那枚银元还是在他身上。
这是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最为关键的一仗。部队前进着,到了腊子口。抬眼望去,周围都是崇山峻岭,东西两侧都是100多米高的陡峭石崖,如刀劈斧削一般,中间是一个宽8米左右的隘口,腊子河从峡口奔涌而出,抬头望去,只见一线青天,地形险要,易守难攻,可谓是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。我问荣全哥:“这里的山和湘西的山哪个更险一点?”荣全哥回答我:“无论是哪里的山,老子都能轻松爬上爬下。”
当时,驻守在腊子口的敌军有两个营,其中一个营扼守隘口,另一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谷地。守军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碉堡,形成交叉的火力网。可谓是易守难攻。下午时,战斗打响。我军计划从正面直接进攻,可敌人凭借地形优势,用机关枪封锁独木桥,加以投掷手榴弹阻止我军接近桥头,正面进攻一直没有进展。半夜时分,部队决定暂停进攻,重新研究作战方案。经过缜密侦察,我们决定成立突击队,兵分两路夺取腊子口,一对隐蔽迂回至腊子口右侧,从崖壁攀登至敌人后侧;另一队则从正面突击,夺取独木桥,若袭击不成,也要连续进攻,达到消耗敌人,造成其恐慌的目的。
我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,悄悄地摸到了桥边,利用桥肚底下的横木,一手倒一手地往对岸运动。敌人发觉后,用机枪、手榴弹朝桥下乱射乱打,我们摸到一块岩石下,待机行动。另外两个突击小组趁敌人火力被吸引至桥下的机会,冲到桥边向敌人掷过去一排手榴弹,紧接着冲进敌人筑在桥头上的工事。我们乘机从岩石下钻了出来,翻上桥面,拔出大刀,喊着冲杀声跟敌人肉搏起来。
天上是红的近乎有些黑的太阳,它放射的光直愣愣的照在我的身上,我的身体好像要被晒下一整块皮来。河水很清,三丈仍可见底,来往着各种形体美丽的船只。船尾被近乎透明的鱼浩荡的追赶着。山头为石灰岩,烧石灰人窑上飘飏着青烟与白烟。有人在喊我。我抬头四处寻找着,山崖上站着一个人,身影雄壮。我问他他是谁,他并不回我,只是从山崖上一跃而下,激起大片水花,船尾的鱼都飞快的朝他游去。一瞬间,四周只剩下我和我的船,我摇起橹,继续前行。
后面听活下来的战士们说,他们摸至腊子口右侧峭壁下,被高达百米的绝壁难住了。荣全哥自告奋勇说到:“老子在湘西的外号可是叫‘云贵川’。”荣全哥用带铁钩的长杆沿峭壁爬了上去,把用绑腿做成的绳索系在大树上垂下来,战士们顺绳索攀上峭壁,迂回至敌人身后,向没有顶盖的敌工事投掷手榴弹,敌人万没想到我军会从峭壁迂回至其后方,惊慌之下士气大泄,被我军两侧夹击,只得仓皇逃命。荣全哥追赶着敌人,在与敌人搏斗时与敌人一起坠下了山崖。
我军乘胜夺占了独木桥,控制了隘口炮楼,随后总攻部队兵分两路,沿腊子河向峡谷纵深扩大战果,连克敌人多道防线,一举夺下腊子口天险。
长征胜利后,我继续当着兵,挣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。偶然有天我办事路过腊子口,顺便去拜访了烈士们的陵园,那属于荣全哥的土包上,一只螳螂静静的立在那,像一名守着陵园的士兵。